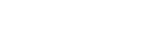《大学之理念最新4篇》
内容简介 篇1
《大学之理念》主要内容:在今日知识经济时代,大学作为发展知识主要的地方,已经成为社会中最重要的一种机体了。大学越变得重要,就越需要对大学之理念与功能作反思。何谓反思?知识是否是一种或一型?大学又是否只是求真,而与美、善无涉?不夸大地说,大学之发展方向关乎到一个国家的文明之性格。
下篇:对大学一些问题的探讨 篇2
在上篇,我们已作了一些对大学之源头、理念与性格的论述。这些看法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当然不能说没有其他的看法。事实上,“什么才是一真正大学?”并非容易有一绝对的答案,且常是争论不休的。同时,我们要知道,大学不是存在于社会的真空的,它是大社会的一个组成。因此,大学的理念与性格不是常永不变的,它不能不因社会之变而有变革。20世纪80年代的今天,大学在教育民主化及知识爆炸的刺激下,大大发展,但大学,特别是克尔的“综集大学”,也出现了种种问题,甚至可虑的危机。在这一篇里,我将提出今日大学所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与挑战,以供大家思索与探讨。
3、 专精与通博
大学教育,自古分科,孔门之学即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南朝宋文帝将大学分为“玄”、“儒”、“文”、“史”四学。西方中古大学亦分文法、修辞及逻辑三科,或算术、几何、音乐及天文四科。学术需专攻,应是无可置疑的。但今日学术专门化越来越烈,越来越细,不止发生施诺(C.P.Snow)所说二个文化之对垒问题,且是“多种文化之相隔”之问题,不止发生“隔行如隔山”之现象,即使同行之学者亦往往无法沟通其所见所学。“道术分裂”一至于此,学术之深度固然加增,但见木不见林,知识之整全性之掌握则戛戛乎难了。诚然,专业化是学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怀海德(Whitehead)且说:“我确信在教育中,你排除专精(specialism),则你摧毁了生命。”今日知识上的许多突破显然与专业化有关,而就大学教育来说,一定程度的分科也是必要的,至于社会之职业结构越来越需专门知识的情形下,学生专修一科一系也是必要的,但大学教育毕竟不应只是训练一技一能之士。一个大学生应该对人类知识文化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对自己民族的学术文化有一基本的欣赏与把握,同时,他应该养成一种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一种对真理、对善、对美等价值之执著的心态。世界大学莫不对于学科综合的问题视为知识学上及教育上的重大挑战。在知识学上如何建立耶士培所说之一有机的整体,煞非易事,即就人文学与科学之整合已经困难重重,更何况集各种学术而冶为一炉?至于教育上则历来莫不在专精与通博上求统合、求平衡,而其方法则有多种:牛津之Modern Greats合政治学、哲学、经济学而治之是一途;英基尔大学(University of Keele)之将第一年定为“基础年”(foundation year),旨在探讨西欧文明之背景、遗产、成就及其问题是另一途;通过科际整合之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又是一途。至于美国之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及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更是最普遍典型的途径。香港中文大学除由大学提供志科教学外,又由书院提供通识教育亦可说是一条值得走的道路。但专精与通博的平衡之路是仍然值得不断探寻的!
[大学之理念]
作者简介 篇3
金耀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校长。著有《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政治与文化》、《剑桥语丝》、《海德堡语丝》等。
一,大学之理念、性格及其问题
上编:大学之源头、理念与性格 篇4
1、 现代大学之源头与原义
大学的起源可以溯到中国的先秦、西方的希腊与罗马,但现代大学之直接源头则是欧洲中古世纪的大学。大学是中古的特殊产物,中古是宗教当阳称尊的世纪,它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向来是学术上缠讼不休的事,但没有人否认大学是中古给后世最可称美的文化遗产。
University一字原无确指,与community、college二字通用,之后,则成为一种特殊的“基尔特”(guild)之称谓。与英文university一字最接近的中古称谓是studium generale,它是指“一个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的地方",而非指“一个教授所有课程的地方”。而中古时universitas一字则指一群老师宿儒(masters)或一群学生所组合的学术性的“基尔特”而言。到了15世纪,studium generMe与universitas二字变成同义,都变成英文university的前身了。
中古大学中以法国的巴黎大学、意大利的勃隆那(Bologna)为最早,或称为中古大学之原型。两者皆是12世纪出现者,其他如英国的牛津、剑桥,意大利的萨里诺(Salemo),德国的海德堡、科隆等,都是中古大学的佼佼者。中古大学与宗教不能分,大学最早是寺院型态,13世纪则是教堂型态,之后才成为基尔特性格,并从宗教中逐渐解放出来。就今日的大学来说,牛津与剑桥可能是最保有中古大学的原趣的,至少牛剑是从中古一脉相传下来,在七八百年无数的变迁中仍然保持了其古典性格的。
中古大学最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世界精神、超国界的性格。14世纪欧洲在学问上有其一统性,它有一共通的语言(拉丁),共同的宗教(基督教),教师和学生可以自由地云游四方,从勃隆那到巴黎,从巴黎到牛津,在同一的上帝的世界里,甲大学的学者可以受到千里外他国乙大学学者的款待,论共通的书,谈共通的问题,宾至如归。中古大学的“世界精神”后来因拉丁语的死亡、宗教的分裂而解体,直到19世纪末时才又渐渐得到复苏,至20世纪则又蔚为风气。现代大学的“超国界”性格的基础则不在共同的语言或宗教,而在科学的思想,而在共认的知识性格。此所以现代大学之间常有学术会议、交换计划等等。
2、 大学的理想与性格
大学的理想和性格几个世纪来已发生许多的变化。第一本给大学系统性地刻画一个明确的图像的重要专著也许是19世纪(1852)的牛津学者纽曼(John H. Cardinal Newman)的《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nity)。纽曼认为大学是一个提供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培育绅士的地方(虽然他也认为大学可以训练职业人才)。他以为大学之目的在“传授”学问而不在“发展”知识。他说:“如果大学的目的在科学的与哲学的发明,那么,我看不出为什么大学应该有学生。”纽曼之书为论大学之经典。他心中大学所应培育之绅士乃指通达而有修养与识见之文化人,此一教育理想影响英国教育甚巨,亦是19世纪牛津、剑桥之教育蕲向。简言之,纽曼之大学理想着重在对古典文化传统之保持,教育之目的则在对一种特殊型态之人的“性格之模铸”(character formation)。纽曼的大学之理念显然是“教学的机构”,是培育“人才”的机构。这个理念也许是古典大学遗留给今日大学教育最重要的遗产。
19世纪末时,大学的性格开始巨大的形变。这一改变始于德国。德国大学亦由中古一脉相传而来,惟到了19世纪末叶时,在洪堡德(Von Humboldt)及阿尔托夫(Ahhoff)等人的革新下,柏林大学首先旧瓶装新酒,彻底改制,摆脱中古的学术传统,标举大学的新理念。他们大学的新理念就是以大学为“研究中心”,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自由地从事于“创造性的学问”。每个学生则如Hemholtz所说,应该至少在日益增大的“知识金庙”上置放一块砖石。这种大学的理念与纽曼所怀抱者迥然不同,因为它所重者在“发展”知识而不在“传授”知识。当然,大学仍把“教学”看作是重要的功能之一。德国这种大学的新理念逐渐影响到欧洲各国,并对美国大学发生根本性的冲击。中国现代教育家蔡元培之改革北京大学就是以德国大学为模式的。在20世纪初时,德国确成为世界大学的耶路撒冷。
德国大学的新理念,在美国大学的先驱者佛兰斯纳(A.Flexner)的《大学》(Universities)一书中获得系统性的阐扬。佛兰斯纳的《大学》一书成于1930年,已被公认为一部论大学的现代经典。他在该书第一篇就标举出“现代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 modern university)。他特别强调“现代大学”,以别于早他七十几年的纽曼之“大学”。佛兰斯纳肯定“研究”对大学之重要,肯定“发展”知识是大学重大功能之一,但他却给“教学”以同样重要的地位。他指出,“成功的研究中心都不能代替大学”,也即大学之目的不止在创发知识,也在培育人才。佛兰斯纳对大学有一整套的看法,他以为大学必须是一“有机体”(organism)。他赞成大学应该探讨“物理世界”、“社群世界”及“美术世界”的种种知识,但他反对大学训练“实务人才”,反对大学开设职业训练(vocmional training)之课程,他也反对大学无限的扩大以破坏它的有机性,他更极力反对大学成为社会的“服务社”(service stmion)。他强调大学应该是“时代的表征”,但他不以为大学应该随社会的风尚、喜恶而乱转,他并不以为大学应该是“象牙塔”,但他强调大学应严肃地批判地把持一些长永的价值意识。
论大学理念的书与文,不知凡几,但德国哲人耶士培(Karl Jaspers)的《大学理念》(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一书却值得特别一提。耶士培此书成于希特勒统治崩解,德国大败,德大学受创极深之际。他以哲人之智慧,筹思人类学术的路向,发挥大学之理念。耶士培以大学之使命只在忠诚于真理之探寻。在他,大学乃是一师生聚合以追探真理为鹄的之社会而已。他认为大学乃为对知识有热情之人而设。真正的大学必须具有三个组成,一是学术性之教学,二是科学与学术性的研究,三是创造性之文化生活。三者不可分,分则必归于衰退。耶士培特别强调大学是一“知识性的社会”(intellectual community),也以此特别强调学术自由与容忍的重要。同时,他也肯定大学教育之目的在模铸整全的人。这就是他所以主张在教学与研究之外,大学更应措意于创造性之文化情调。从理想上说,师生之间应该有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耶士培重视大学之尊严与独立性,以大学为“国中之一国”,但他不以为大学可遗世独立,故他极力主张把“技术”(technology)引进大学,并以为技术在大学应占一中心位置。[许多古典大学如牛津、剑桥都以技术不登大雅之堂,而长久以来均加以拒斥。但目前则已有变。就此点言,剑桥的艾雪培(Eric Ashby)爵士可说是耶士培的同道,艾雪培且高唱出“技术人文主义”的理论。]耶士培相信组织的整全性,大学的整全性,他认为了解事物现象之整全性是人之求知欲的锁钥。但知识之发展却不能不靠分工,知识的深度尤不能不依赖学术的专精。事实上,学问上分为院系可以追索到中古大学。耶士培不反对学术之专门化,但他强调知识应该有一整全的存在。大学应该是一有机的整体,在中古大学,这种整全性与有机性是存在的,但他以为今日的大学都成为一组无所关连的学科的聚合,并没有整全的有机性。当然,我们不能回到中古,但现代不断膨胀的知识与研究又应如何在大学中加以整合呢?关于这一点耶士培与佛兰斯纳一样,都提出了很多的理念,很好的问题,但却并没有真正有力的答案。
自二次大战之后,大学教育在世界各地都有蓬勃的发展。而在美国尤其获得快速与惊人的成长。在1876年前,美国只有书院(college),还谈不上有真正的大学,而此后在吉尔曼(Gilman)与艾略特(Charles Eliot)等人的改革发展下,步德国大学的后尘,才一步步提高大学的水准。二次大战以来,美国大学不但在量上言为举世之冠;在质上言,其一流学府,如哈佛、柏克莱、芝加哥、耶鲁等较之欧洲任何大学亦毫不逊色且或更有过之。时至今日,论者几莫不以美国为当代大学之重镇。美国大学之发展自与其国力交光互影,彼此影响着。讲美国大学,当然需知其品流参差,但我们所应注意者则是那具有领导性地位的大学,看看它们的理念与性格。就我所知,对美国大学之发展极深了解而能掌握其精神面貌的是前加州大学校长克尔(Clark Kerr)。克尔的《大学之功能》(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一书,其论点与见解极多挑激性,是了解当代大学不可不读之书。美国的先进大学,一方面承继德国大学重研究之传统,一方面也承继英国大学重教学之传统。我们可说,美国的研究院采德国模式,大学部则多少受英国影响。但当代的美国大学,如克尔所指出,早已越出了德、英的模式,而发展出自我的性格。美国的大学狂热地求新,求适应社会之变,求赶上时代,大学已经彻底地参与到社会中去。由于知识的爆炸及社会各业发展对知识之倚赖与需要,大学已成为“知识工业”(knowledgeindustry)之重地。学术与市场已经结合,大学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象牙塔内与象牙塔外的界线越来越淡漠,甚至泯灭了。大学内部则学生可以多达五六万,甚至十万以上;学术之专化更是惊人,如整个加州大学课程之多竟达一万门之数,不但隔行如隔山,即使同行的人也是无法作有意义的交流。而教授之用心着力所在多系研究,教学则越来越被忽视。教授的忠诚对象已不是大学,毋宁是支持他研究的福特基金会、西屋公司或华盛顿。一个教授所关心的不是他隔壁他行的同事的评价,而是其他大学乃至其他国家的大学的同行的评价。大学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它的成员已不限于传统的教师、行政人员和学生,还包括许多“非教师”的教学人员(如研究教授),它的组织已不止限于学院(faculty)、书院(college),还包括无数的研究中心、出版社、交换计划中心……他的活动已不止限于研究、教学,还包括对外的咨询,与国外的合作(加州大学的研究计划涉及五十几个国家)等等。总之,在数量、组织、成员、活动各方面,今日美国的大学与以前的大学已大大不同。这种大学的理念及性格与纽曼的构想固然相去十万八千里,与佛兰斯纳、耶士培的构想也迥然有别。克尔认为纽曼心目中的大学只是一“乡村”,佛兰斯纳心目中的大学也只是一“市镇”,而当代的大学则是一五光十色的“城市”了。克尔对美国大学的巨变虽然认为不是没有问题,但他显然是乐观而正面地加以肯定的。他同意哥顿(D.S.Gordon)所说真正的美国大学,还在未来。但他肯定今日的美国大学将成为世界各大学的模型。克尔给今日美国大学一个新的称呼,即multiversity(勉译为“综集大学”)。因为它的性格已不是university一字所能表达了。克尔的multiversity一词确是神来之笔,因为它的确很象征化地表显了当代大学的性格。诚如他所说,今日大学不再是佛兰斯纳所说的“有机体”,不再具有统一性,而毋宁是一多元体,并具有高度的多样性。他老老实实地说,multiversity不是一个和谐合调的组织,它也不是一个“社会”(如耶士培所说的大学是一“知识性的社会”),而是许多个不同的社会,或者说是一个多种目的之多元性社会。在此,我们先不必对克尔的“综集大学”的概念加以批评,但要指出,克尔的确很有力而生动地描绘了当代美国居领导地位之大学的性格与动向。事实上,他并没有太夸张,美国这种大学的理念与性格确已越来越为其他国家的大学有意或无意地视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