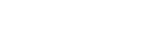《一念相思一寸疼痛散文》
一念相思,一寸疼痛
活着,便是要历经岁月的沧桑,渐或磨平世间的沟壑,却抚不平我内心的悲凉。一念相思,一寸疼痛,裸露在时光下,渗出一抹嫣红的惦念和怀想。
——题记
◎柠檬花下
三月,阳光温热,柔软得如绸缎上的锦绣时光。人面桃花灿然,岁月这般静好,您却走了。时过境迁,故人难见。梨花香呵心却感伤,愁断肠,千杯酒解思量。柠檬花下相思未央。
二十九日凌晨三点,您走得太突然了。我来不及相信。此时,我的眼泪沾湿了枕头,睡不了,天一亮就回家,见您最后的一面吧,疼……
哭红了眼,声音在黑暗里抽离沙哑,静静等候黎明的到来。
早晨,寒凉袭来,我的心苍茫空尽,潦倒着荒原一路蔓延,像索然之冬飘落晶莹眼泪的雪花凝落于我的眼角和手心……
踏上汽车,寻找回家的路,我呆呆地望着风景嫣然的季节,心突然漏掉了半截。
我只是希望,您是在和我们开开玩笑,等您睡一觉就起来,伸着双手,呼吸着新鲜空气,轻轻唤着家里的孩子们。
可是,在我归时的途中,证实了您走了。我才发现您离我们越来越远,坐在车位上,一直哭一直掉眼泪。
沿途的花花草草在阳光下,如此的美丽。但我,却不知道如何去丈量我和您的距离,您闭眼的那一瞬间,我们都只是在梦中。
无法守着您最后的灵魂抽离,我们只有任凭眼泪坠落。
您,真的走了。此刻您是否在等待归来的孩子们?
随着汽车的颠簸,我的记忆开始充血。
最后的一个电话,是我嘱咐您和爷爷多买点盐放在家里。一个电话竟然成了生与死的别离。您问我,枚子,何时回来看看奶奶啊。我说,五一大假,您老的八十大寿就回来,我准备了一份大礼呢,奶奶。
您只说了一句,好,记得早点回来。
只是没有想到,回来便是要送你最后一程。这是多讽刺的场面。
推开车窗,我的视线里犹如散落了一路的火纸,在风驰下,竟翩缱成黄色的蝶,无力地低垂着。它们是护送您回家的证明么?是您回家落下的寂寞痕迹么?
心骤然抽搐,泪早已崩溃。
平坦的公路,客车飞奔疾驰而过,我离家越来越近了。路过您和爷爷住的街头那房子,木木地凝视那一扇门,我渴望您静候在那扇门口,在阳光下,闪烁着银白的光阴,安然听着我们唤您一声奶奶。可是,今天,那道门紧闭着,我知道您回了乡下的老屋。
从桥头下车,这短短的几百米,我竟然像走了一个世纪那样漫长,您越来越远了,我该怎样测量这种距离?
脚步慢慢地挪动,提着相思的口袋,站在浅念起风的渡口。仿若此时,反反复复的听着那一曲您曾深爱的京剧,也不过只剩余了一些依稀相似的聒噪;仿若此时,您低首看着手中的青花茶杯,纹路依然分明,只是往日钟爱的柠檬茶已换成了深褐色的苦丁茶……刹那恍惚,突然不认识了这里是哪?
我看着叔伯们头上一抹白色,便惊寒得抽离,含着眼泪,搁下行李,扑通跪拜在您的面前。您依旧那般慈祥,那般和蔼,紧皱的眉头该是疼痛的煎熬。您静静地躺在寒凉的冰棺里,花白的发间微微升起白色的水雾,双手双脚无力地垂落着。他们怕你冷,为您盖上厚厚的被子,足足六床被子,也权当是六个子女为您捂热归去的路。
两只木质的拐杖,跟随着您已经有二十几年了,它被您摩擦得光洁透亮。老伙计斜斜歪歪地靠在您的身边。
爸爸说,您在闭眼的那一刹那,双手吃力地指着的就是它,我知道您舍不得它,更是想回家,人都想落叶归根。可是年幼的堂弟城,哪懂您的`心,让您死不瞑目。
在爸爸的坚持下,把您安放在家里新修的三层楼房里,您说过,您想回老家住一下新房。
我默默地流着眼泪,褪下了花红柳绿,穿起了黑色的衣服黑色的裤子黑色的布鞋,手臂带上写有挽的袖肩,头上裹着三尺白绫,拖延着长长的思念。香烛弥漫着清晰可见的袅绕,缠绕在梦靥边缘;唢呐吹响着生命的终结,丧鼓锣儿敲击着沉重的步履,安送逝者的灵魂;哭丧歌人低沉平仄的语调抚慰逝者飘散的神聚。我们作为晚辈唯一能做的是默念,在夜深宁静的上空,盘旋着思量与追悼,凝结着厚实的眷恋与不舍……
叔伯们整理着您的遗物,在几本破旧的书里,夹着厚厚一叠人民币。隔几页放一沓,足足存了八千一百块钱。基本是按照家里六个子女一人一千,老伴一千,每个孙辈一百的发财钱。
虽然,这些钱并不多,但是,对于省吃俭用的您来讲,是个巨大的数字。因为,这是您做卖一双双布鞋换来的。
望着这些钱,家里的每一个人,都默默地哭着,为您滴血。
翻开箱子,看见几包鞋子,写着我们四个孙女的小名。这是您为我们准备的婚嫁布鞋。一人二十多双,您知道我们的母亲不会做,而我们已经到了快出嫁的年龄。
您说过,从前女子出嫁,母亲都要提前给女儿准备婚嫁布鞋,祝愿女儿婚姻步步生辉,平安喜乐。您代替我们四个孙女的妈妈为我们准备了。
而,堂叔表叔们也抹着眼泪,说您也给每家的侄儿侄媳一人做了一双布鞋。手抚摸着灯草绒的脚面,很是暖和。
突然,我的眼前呈现出您戴着老花镜,在晨光微弱的门口,安然坐着,捻一根白色的线,使劲扎进鞋底里,密密细细的针脚,是岁月的镌刻,是爱的雕饰。
每年,我们六个家庭都会收到您为我们所有人做的布鞋。只是我们当中的有些人,爱慕了虚荣,蹬起了皮鞋,把布鞋压了箱底。
收起所有的遗物,我们齐刷刷地跪在灵前,磕破了额头,在您的面前尽最后一份孝,陪您走过尘世里的最后十五天。
风微凉,夜未央,孤灯烁,把思量。在每天的油灯燃烧下,我们铺着谷草,铺着被褥,安静地睡着您的身边。
夜,很凉,哭丧歌人的音律响彻在四月烟雨中,几多凄凉,几多伤感。哭了,累了,倒了,病了,伤了。
我们为您渐宽衣带不悔,我们为您消得人憔悴。
在短暂的十几天里,我们全家二十五口人,一点荤油都不沾,瘦了脸颊,瘦了相思。有人说月亮弯的时候,思念也弯;月亮圆的时候,思念也圆。那半个月,月亮也病了,瘦成一弯眉。
下葬那一天,看着片片白幡在那光秃脊梁上又添荒凉的坟前立着,纠结着,默哀着;声声鞭炮停驻归人脚步,沉重着,无奈着;袅袅轻烟点燃亲人缕缕相思,飘散着,哀叹着。山坡上,自家的柠檬花,散漫着沁入心脾的花香,随风撒落在奶奶的坟前,白色的花蕊,挂着一个个青色的果实。
我明白,柠檬花下,是您钟爱的归宿,嗅着春天的气息,守候着您挚爱的土地,来年,可赠送一季花开春暖,秋果累累。
此时天空,飘起了雨儿,漫洒下一路泥泞,一路飘撒着雨的忧思,清明将至,把远方归人的魂引入了这片天空,我们一大家子几十号人,浩浩荡荡的走向山岗。
让我们再看您一眼,从此把您印在心上。一抔黄土,将是您最后的皈依;一树柠檬花,将是您今生最好的陪伴。我静静伫立在墓碑前,看您,静静的感伤,碑上的笑颜很美很美,也幸福。您像只是睡着了一样,安详宁静。
我伫立在柠檬花下,恍然看见您化成了一只嫩绿色的蝶盘旋在我们的身边,大家哭了,您停在岁月的枝头,静静地凝视着我们,叫我们别哭泣,在岁月的痕迹里,默然守候着那些眷恋,那些爱。风起,您就轻盈的飘然远走,飞向遥远的国度……
◎橘子红了
朋友从乡下老家,提了一大袋柑橘,说是自家树上摘下来的,绝对无害水果,让我们放心吃。瞬间,朋友们蜂涌地去抢。因为没有农药侵蚀,长相实在有点抱歉,坑坑洼洼的,不过呢,倒也小巧玲珑。
一个长相如月球表面的柑橘,指尖轻触,凉凉悠悠的,长长的指甲嵌进果皮,倏地剥开,溅起一层层油脂,伴有淡淡的清香,桔黄色的果肉,放在唇边,便是爱不释手了,甘甜,多汁,极好的味道充斥在我的喉咙间。
如此好吃的柑橘,让我有些爱不释手,放纵自已多吃了几个。偏爱这种酸酸甜甜味道的还源于外公。
外公家居住在大山里的,山高地险,丛林茂盛,良田基本没有,几分薄土倒任由时光耕种。
那种家中少食多嘴的年代,靠几分贫瘠的土地,无法折腾出更多的吃食和口粮。
好在,外公懂些果树栽培,从重庆大足小舅公家那讨来了些柑橘树,在后山开垦了几亩荒山,小心栽植,小心伺候着,定时培土,定时施农家肥,定期给柑橘树们修枝剪叶,终在秋冬季获得满园橘红色的小灯笼,向我的母辈们宣告橘子红了。听母亲说,她们儿时最高兴的莫过于在秋光下尝着那些甘甜。
日子恰如流沙,母亲和姨们相继结婚成家,外公更是把所有的心血付诸于这一片柑橘林,不辞辛劳。
记忆最清楚的是七岁那年,四川的天空在小寒时节飘起了雨夹雪。外公的柑橘林,眼看就可以高挂红灯笼,卖钱了,可惜,这天公不作美,让它们在这种潮寒的天气里,越发溃烂。
这如何也是来不及摘卖的,何况市场价格也不过是几分钱般贱买,有时候在寒颤的风口下,双手交错缩在衣袖里,头踡缩着,双脚跺步,也卖不出去几斤柑橘。
为此,外公总托熟人让我妈和三姨去摘柑橘,挑回来给外孙们吃。
每次母亲都会挑回满满一担,橘红色的表面渗着一层水滴,在昏黄的灯光下,倒像橘色宝贝,硕大,鲜艳。直勾勾地垂涎着它们的清甜和芬芳。
在物质贫乏的八十年代,生活中的水果,仅限于乡土生长的五月李子,七八月的地瓜(是藤蔓下一颗颗粉红色的植物果实),寒冬时节的柑橘。
秋冬时节,嘴唇干裂,渴望汁水滋养,母亲从外公家摘回来的柑橘无疑成了解馋的救赎。
母亲一声令下,我们姐仨迫不及待地去筐里拿,使劲剥,使劲往嘴里塞。大吃海塞,把肚子撑得鼓鼓的,告知父母,晚饭不吃了,洗脚上床瞌睡了。
连续几天接着吃,直到吃没了,还是心心念念,便和姐弟背上扁篼,兴冲冲地绕着山路,一深一浅地迈在外公家的路上。夜幕下,小路极难走,要翻山越岭的,穿过荆棘,越过阴森的空旷,寒风料峭潜入那片夜色中,瑟瑟的枯叶唏唏嗦嗦地散场,以哭砂的姿态作自杀状。闪烁的光影倒映在身后的竹林、青冈林,荒芜的坟茔扯着噪子吼着,晃悠着幽怨穿越岁月,我们姐弟三人抱团,心慌意乱,加快了步伐,试图甩落了鬼魅影绰,远远看见外公家那盏灯光,心便锃亮明净!
即便如此,仍让我们惦记树上那一片探出来的小脑袋。天亮,外公便带着我们,爬上后山,手里拿一根弯钩,背上一个大大的箩筐。
走进那一片橘园,到处蔓延着喜庆的招摇,清风拂过,小家伙们一个个地探着头,打量着我们。清晨,橘子们满身裹满羞涩,娇羞地掩藏在树叶底下,时不时地可怜着我们的矮小,温柔的弯下腰,轻抚着我们的脸庞,亲吻着我们的鼻子,甚是可爱极了。
看着这样的盛景,我不由闭上双眼,静静地沉醉在这橘香的世界,陶醉在那甜甜的味道里。如若不是姐姐的一句话,我肯定是得发呆一上午了。盯着姐姐那单薄的身体,我不由替她担心,便把她叫了下来,自己一骨碌爬上高高的树枝上,伸手便要擒住我内心那一片颜色,美得无与伦比,它们是可爱的孩子,更是乖巧的孩子,摘下便丢给在树下雀跃的弟弟,他实在太小,实在太文静,这种与刺打交道的活,本就不是他俩可以干的。外公也在树下忙忙碌碌的,时时地叮嘱我,小心摔着。
望着外公慈祥的脸,砸人而花白的胡须,傻傻地冲他笑着。如今,想来都还那么清晰。因为小时候,我是由外公带大的,总爱跟在他的屁股后面放牛割草,爬山什麽的。
一筐橘子,没用多久就满载而归了,外公看着我们的傻样子,乐呵呵的。我想他是觉得很有成就感吧,所有的外孙们都偏爱这片橘园,那是外公带给我们的欢乐和甘甜。
十岁那年,外公因病离开了我们,遵照他老人家的嘱咐,把他葬在那一片他深爱过的橘园里,他说他想听橘子的花开花落,更想听我们在这片橘园里欢快的歌声。
外公走了,走在那一片橘红里,走在那一年的寒冬里,来不及咂吧他的橘红,留下一杆旱烟磕巴着岁月的痕迹。
从此,橘园,就没人打理了,每年总是稀稀拉拉地挂着几个橘子,表示它们还活着,渐渐地它们也老了,死气沉沉地挂着风霜雨雪。
转眼,十七八年过去了,橘园里的树,被虫子们吃空了树干,乳白色的木屑从一棵棵树下剥离,树枝早已干枯,歪歪溜溜地倒在那一片橘园,整个果园里,满地都是一两米的杂草,苦蒿草留着青涩的泪,垂卧在外公的坟前。
大年三十,父亲带着我,提着一瓶酒,一碟花生米,一盘卤肉,一盘水果,有苹果,香蕉,雪梨,桂圆,还有外公生前爱吃的橘子。一柱香,焚然缭绕着这隔空离世的思念;一封鞭炮,响彻于大山深处,及时地告诉他,过年了,我们来看看他老人家;一个磕头跪拜,曲腿扣心念故人。仰望天空,便是橘子红了,相思未央。
风声起,父亲拔着坟头那些杂草,他知道外公爱干净,父亲的喃喃自语,像是在和外公对话,听着舒心的话语,我满眼溢满的泪,挂在腮边,来不及擦拭,转身,静默在焚香中听着旧日里的笑声朗朗,看着外公矍铄的眼神。
祭拜结束后,父亲说,拿着吃吧,这是供果,你外公特许你吃的。吃着这样的橘子,任凭思绪蔓延,春去春又回来,花落花又开,冥冥之中的安排,谁能抵挡?橘子红了,欢颜旧在;橘子红了,丛生的想念,像野草遍及爱的荒原;橘子红了,红透了我对亲人的惦念。
而今孤身异乡的我,时钟指向了凌晨一点半,我蜷缩在夜里,发着抖,想念外公,用尽笔下的墨迹,勾勒出外公的样子,有人说我太痴,太傻。任由键盘候住指尖缭绕着思念,在这宁谧的夜里,轻缓脉动血管里的浅殇。今夜,我的心悬挂在无风月的时空里,相思,未央;在花前月下,缱绻,深情。可别问我成因,只待梦里花落方可知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