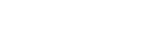《小学生故事2020汇集》
对于小学生来说,多看一些励志类的小故事,不仅可以丰富自己的阅读量,还可以学到很多的大道理哦!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关于小学生故事,方便大家学习。
小学生故事1
让计划让位于行动
奥马尔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的头脑里充满了智慧,而且稳健、博学,为人们所敬仰。有一次,一个年轻人问他:”您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刚—开始您是否就已经制定了—生的计划了呢?“奥马尔微笑说:”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我才知道制定计划是没有用的。“当我20岁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要用20岁以后的第一个10年学习知识;第二个10年去国外旅行;第三个10年,我要和一个漂亮的姑娘结婚并且生几个孩子。
在最后的10年里,我将在乡村地区,过着隐居生活,思考人生。“终于有一天,在前10年的第7个年头,我发现自已什么也没有学到,于是我推迟了旅行的安排。在以后的4午时间里,我学习了法律。并且成了这一领域举足轻重自的人物,人们把我当作楷模。这个时候我想要出去旅行了,这是我心仪已久的愿望。但是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无法抽身离开。我害怕人们在背后斥责我不负责任,后来我只好放弃旅行的想法。等到我40岁的时候,我开始考虑自己的婚姻了。但总是找不到自己以前想像中那样美丽的姑娘。直到62岁的时候,我还是单身一个人,那时候我为自己这么大一把年纪还想结婚而感到羞愧。于是我又放弃了找到这样一个姑娘并且和她结婚的想法。后来我想到了最后一个愿望,那扰是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隐居下来。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如果患上疾病,我连这个愿望都完成不了。这就是我一生的计划,但是一个也没有实现。”年轻人,不要把时间放在制定漫长的计划上,只要你想到要做一什事就马上去做。放弃计划,立刻行动吧!“奥马尔最后说。
点评:在孩子学习的过程中,与其给孩子制定漫长的学习计划,不如督促孩子立即开始行动,把握好当下的时光。在具体行动中,或许会有新的发现,或许会有新的想法。如果适时做出调整,或许能够找到更适合自己孩子成长、发展的新办法和新途径。
小学生故事2
油灯的光芒依旧
一名学生因为怕麻烦老师,所以总是不敢问问题。这个老师非常细心,经过长时间和学生们的相处,老师终于发现了这个现象,就问他原因。学生说:”老师,很抱歉。您给我的答案我又忘记了。我很想再次请教您,但想到我已经麻烦您许多次了,就不敢再去打扰您了!“老师想了想,对他说:”你先去点一盏灯。“学生照做了。老师接着又说:”再去多拿几盏油灯来,用第一盏灯去点燃它们。“学生也照做了。这时老师笑着对他说:”其他油灯都是用第一盏灯点燃的,但是第一盏灯的光芒有损失吗?“学生回答道:”没有啊!“老师又对他说:”和你们分享我所拥有的知识,我不但不会有损失,反而会有更大的快乐和满足。所以,有问题的时候,欢迎你随时来找我。“
点评:家长应该让孩子知道,一个人的知识是很有限的,但经过多人长时间的互相讨论、请教,他们的知识和底蕴都会有所提高,所以,如果遇到什么问题你不会不懂,就去问别人。请教也是一门学问,每时每刻都可以去请教,只是请教的对象不同,有直接,有间接。可以向书本请教,也可以向同学、老师和家长请教。没有请教就没有进步,就没有成功。
小学生故事3
上世纪50年代初,巴菲特毕业后,办了一家小公司,但经营异常惨淡。
他落魄地来到老师身边,倒了许多苦水后沮丧地说:“我已经用上了我所有的知识和经验,可我为什么还无法成功呢?”
老师把巴菲特带到教室里,拿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三个点,说:“请用一条线将这三点连起来!”
巴菲特有些纳闷地接过粉笔,然后轻易地画出了一条直线。
老师点了点头,接过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九个点,像一个“田”字。老师再次把粉笔递向巴菲特,说:“你再用一条线把这九个点连起来!”
这一次,无论是横画、竖画还是斜着画,甚至动用了所有几何知识,巴菲特依旧无法做到一条直线连起三排九个点。
老师把粉笔横压在黑板上,然后“唰”的一声划去,顿时黑板上山现了一条宽直线,刚好把那九个点全“掩盖”在了里面!
老师意味深长地说:“你认为粉笔只有一种握法,但事实上,它还可以横过来写,而这些,任何老师和书本都没有教过你。你所有的知识与经验也一样,你不能用固有的知识做出死板的判断,所以不能只按照理论走现实中的每一步,你必须要与众不同、独辟蹊径,只有这样,你才能获得成功!”
小学生故事4
美国盐湖城冬奥会期间,当地的邦尼维尔小学邀请中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到学校联欢。联欢会在校礼堂举行,例行的嘉宾致辞、演节目、合影之后,中国驻美使馆的文化参赞上台宣布说,他带来了两个大熊猫玩具。
“我把大熊猫送给两位同学,一个送给学习成绩最好的男同学,另一个送给学习成绩最好的女同学。”
孩子们似乎没有听懂他的话,表情一片茫然。难道孩子们不喜欢大熊猫?
邦尼维尔小学有五个中国孩子,其中一个孩子的母亲晚上打电话说,那两个大熊猫给学校出了个小小的难题。“你知道,美国的小学教育是不强调名次的,根本没有谁的学习成绩最好最坏这个概念。我女儿只知道自己的分数,从来不知道别人的分数。”这位母亲说。
“那两个大熊猫是怎么处理的?”
“学校一开始也不知道该给谁。大使馆送的熊猫脖子上有一条彩带,写着给最好的男孩和女孩。学校想了个办法,改成了送给男孩们和女孩子们。这样,学校将永久保存这两个大熊猫玩具。”
小学生故事5
我七岁入学,入学前父母带着我去照相馆拍了张全身像,照片上我身穿仿制的军装,手执一本红宝书放在胸前,咧着嘴快乐地笑着,这张照片后来成为我人生最初阶段的留念。
我上的小学从前是座耶稣堂,校门朝向大街,从不高的围墙上方望进去,可以看见礼拜堂的青砖建筑,礼拜堂早就被改成学校的小会堂了。一棵本地罕见的老棕榈树长在校门里侧。从1969年秋季开始,棕榈树下的这所小学成为我的第一所学校。
我记得初入学堂在空地上排队的情景,一年级的教室在从前传教士居住的小楼里,楼前一排漆成蓝色的木栅栏,木栅栏前竖着一块红色的铁质标语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标语的内容耳熟能详。学校里总是有什么东西给你带来惊喜,比如楼前的紫荆正开满了花朵、它的圆叶摊在手心能击打出异常清脆的响声;比如围墙下的滑梯和木马,虽然木质已近乎腐朽,但它们仍然是孩子们难得享用的大玩具,天真好动的孩子都涌上去,剩下一些循规蹈矩的乖孩子站着观望。
入学第一天是慌张而亢奋的一天,但我也有了我的不快,因为排座位的时候,老师把我和一个姓王的女孩排在一张课桌上,而且是第一排。我讨厌坐在第一排,第一排给人以某种弱小可怜的感觉;我更讨厌与那个女孩同桌,因为她邋遢而呆板,别的女孩都穿着花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唯独她穿着打了补丁的蓝裤子,而且她的脸上布满鼻涕的痕迹。我的同桌始终用一种受惊的目光朝我窥望,我看见她把毛主席的红宝书放在一只铝碗里,铝碗有柄,她就一直把铝碗端来端去的,显得有点可笑,但这样携带红宝书肯定是她家长的吩咐。
所以入学第一天我侧着脸和身子坐在课堂里,心中一直为我不如意的座位愤愤不平。
启蒙老师姓陈,当时大约五十岁的样子,关于她的历史现在已无从查访,只记得她是湖南人,丈夫死了,多年来她与女儿相依为命,住在学校唯一一间宿舍里,其实也就是一年级教室的楼上。现在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陈老师的齐耳短发已经斑白,颧骨略高,眼睛细长但明亮如灯,记得她常年穿着灰色的上衣和黑布鞋子,气质洁净而优雅。当她站在初入学堂的孩子们面前,他们或许会以她作参照形成此后一生的某个标准:一个女教师就应该有这种明亮的眼神和善良的微笑,应该有这种动听而不失力度的女中音,她的教鞭应该笔直地放在课本上,而不是常常提起来敲击孩子们的头顶。
一加一等于二。
b、p、m、f,a、o、e、i,这才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天籁,我记得是陈老师教会了我加减法运算和汉语拼音。一年级的时候我学会了多少汉字?二百个?三百个?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我就是用那些词汇给陈老师写了一张小字报。那是荒.唐年代里席卷学校的潮流,广播里每天都在号召人们向路线开火,于是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就向陈老师开火了,我们歪歪斜斜地写字指出陈老师上课敲过桌子,我们认为那就是广播里天天批判的“师道尊严”。
我想陈老师肯定看见了贴在一年级墙上的小字报,她会作何反应?我记得她在课堂一如既往地微笑着,下课时她走过我身边,只是伸出手在我脑袋上轻轻抚摸了一下。那么轻轻的一次抚摸,是1969年的一篇凄凉的教育诗。我以这种荒.唐的方式投桃报李,虽然是幼稚和时尚之错,但时隔二十多年想起这件事仍然有一种心痛的感觉。
上二年级的时候陈老师和女儿离开了学校。走的时候她患了青光眼,几乎失去了视力,都说那是因为长期在灯下熬夜的结果。记得是一个秋天的黄昏,我在街上走,看见一辆三轮车慢慢地驶过来,车上坐着陈老师母女,母女俩其实是挤在两只旧皮箱和书堆中间。看来她们真的要回湖南老家了,我下意识地大叫了一声陈老师,然后就躲在别人家的门洞里了。我记得陈老师喊着我的名字朝我挥手,我听见她对我喊:天快黑了,快回家去吧。我突然想起她患了眼疾看不清是我,怎么知道是我在街上叫喊?继而想到陈老师是根据声音分辨她的四十多个学生的,不管在哪里,不管什么时候,老师们往往能准确无误地喊出每一个学生的名字。
我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陈老师,假如她还健在,现在已是古稀之年了。或许每个人都难以忘记他的启蒙老师,而在我看来,陈老师已经成为混乱年代里一盏美好的路灯,她在一个孩子混沌的心灵里投下了多少美好的光辉,陪他走上漫长多变的人生旅途。时光之箭射落岁月的枯枝败叶,有些事物却一年年呈现新绿的色泽,正如我对启蒙教师陈老师的回忆。我女儿眼看也要背起书包去上学了,每次带着她经过那所耶稣堂改建的学校时,我就告诉女儿,那是爸爸小时候上学的地方,而我的耳边依稀响起二十多年前陈老师的声音:天快黑了,快回家去吧。
我从来不知道我童年时就读的小学校的老师一直记着我。我的侄子现在就在那所小学读书,有一次回家乡时,侄子对我说:我们老师知道你的,她说你是个作家,你是作家吗?我含糊其辞,我侄子又说,我们老师说,她教过你语文的,她教过你吗?我不停地点头称是,心中受到了某种莫名的震动。我想象那些目睹我童年成长的小学老师是如何谈论我的,想象那些老师现在的模样,突然意识到一个人会拥有许多不曾预料的牵挂你的人,他们牵挂着你,而你实际上已经把他们远远地抛到记忆的角落中了。
那所由天主教堂改建的小学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美好而生动的,但我从未想过再进去看一看,因为我害怕遇见教过我的老师。偶尔地与朋友谈到此处,发现他们竟然也有类似的想法。我不知道这么做是不是好,我想大概许多人都有像我一样的想法吧,他们习惯于把某部分生活完整不变地封存在记忆中。离开母校20年以后,我收到了母校校庆70周年的邀请函。在驶往家乡的火车上我猜测着旅客们各自的旅行目的,我想那肯定都与每人的现实生活有密切关联,像我这样的旅行,一次为了童年为了记忆的旅行,大概是比较特殊的了。
一个秋阳高照的午后,我又回到了我的小学,孩子们吹奏着乐曲欢迎每一个参加庆典的客人。我刚走到教学楼的走廊上,一位曾教过我数学的女教师快步迎来,她大声叫我的名字,说,你记得我吗?我当然记得,事实上我一直记得每一位教过我的老师的名字,让我不安的是她这么快步向我迎来,而不是我以学生之礼叩见我的老师。后来我又遇见了当初特别疼爱我的一位老教师,她早已退休在家了,她说要是在大街上她肯定认不出我来了,她说,你小时候特别文静,像个女孩子似的。我相信那是我留在她记忆中的一个印象,她对几千名学生的几千个印象中的一个印象,虽然这个印象使我有点窘迫,但我却为此感动。
就是那位白发的女教师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穿过走廊来到另一个教室,那里有更多的教过我的老师注视着我。或者说是我紧紧地握着女教师的手,在那个时刻我眼前浮现出二十多年前一次春游的情景,那位女教师也是这样握着我的手,把我领到卡车的司机室里,她对司机说,这孩子生病刚好,让他坐在你旁边。
一切都如此清晰。
我忘了说,我的母校两年前迁移了新址。现在的那所小学,教室和操场并无旧痕可寻,但我寻回了许多感情和记忆。事实上我记得的永远是属于我的小学,而那些尘封的记忆之页偶尔被翻动一下,抹去的只是灰尘,记忆仍然完好无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