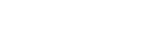《少年派奇幻漂流影评【优秀3篇】》
少年派奇幻漂流影评 篇1
据说最高境界是“手中无刀,心中有刀”,所以,究竟是一人一虎还是有人无虎,已经不重要了,就像片中主人公派说的那样,关键在于你愿意选择相信哪个版本。派是个怪人,搁古希腊,这名字(的数学含义)就会让他命丧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之手;搁现代,同时信仰印度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行为,连他的父母也觉得不可理喻(我一度误以为派是巴哈伊教徒)。派的经历让人想起鲁滨逊,不过,笛福笔下的18世纪人文主义气息已经让位于马特尔-李安所营造的对于人与自然、与宗教之间关系的重审思考,老虎不是“星期五”,虽然派驯服它的过程跟鲁滨逊收服“星期五”的行为有些类似,但派也说了,最后的结局是他留恋老虎而老虎头也不回的弃他而去;再者,在另外一个“现实主义”的惨烈版本中,派就是那只老虎。
有着“广泛”信仰的派身上甚至闪现出泛灵论者的影子,譬如他认为动物也是有灵魂的,这无疑反映出在21世纪的今天,艺术家的创作散发出愈加浓厚的生态主义气息,倒退一个多世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笔下的男孩莫格里,可是以战胜邪恶老虎而享誉文坛的——荏苒百年,派和莫格里,都是跟老虎打交道的男孩,他们对待老虎的态度却截然相反。
李安基本忠实的还原了马特尔的原着:作家对成年派的追访、派诉说的与虎同船的故事,以及最后派跟两个日本人叙述的绝境中人吃人的悲惨遭遇,在片中算是原汁原味的得到了还原(最后那段纯靠对白)。电影的拍摄难度很高,孩子、动物、水、3D,李安这一次啃的,全是硬骨头。常言道“画鬼容易画狗难”,用CG活活的造出一只老虎,比《指环王》里“咕噜”的难度系数其实大多了,从最终效果来看,李安很成功。形式与内容、娱乐与情怀、特效与内涵,本就不是天然对立的概念,这一次,李安又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技术、资本本身没有“原罪”,就看你怎么用——厚重的哲理意涵和炫目的视觉呈现完全可以相得益彰。
派跟老虎在海难后的遭遇,充满了奇幻色彩:巨鲸跃空、飞鱼掠海、风暴来袭、食人魔岛,都给了李安巨大的创作空间,马特尔的文字再生动,也不如被李安化为光影后来得震撼——如果你只想看视觉奇观,我觉得《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也完全合格。
即使在最苦难的绝境中,派对神的信仰也从未动摇,电闪雷鸣中的救生艇就是一叶微舟,脆弱的生命危在旦夕,但派把这看成是神迹的显现,他甚至大喊着老虎的名字,希望它也能出来看看“神”——套用里尔克的诗句,在那一刻,派“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祛魅”(韦伯语)后的现代社会让神隐退,所以,那两个日本人要求派要讲一个“公司能接受”、“大家能相信”的故事版本,这才有了人吃人的情节,而马特尔-李安却一再提醒我们,这是一个“让你相信上帝”的故事。作家选择相信有老虎的那个故事版本,派说:“谢谢你,你选择了跟随上帝”。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猛虎,派的故事启示我们,如果你信神,那事情就会变得像萨松所写的那样:“我心有猛虎在细嗅着蔷薇”。
派能背那么多位圆周率,派是个天才。
在经历过惨绝人寰的困境后,派依然信神。派很幸福。
少年派奇幻漂流影评 篇2
“我完全不顾父愿,甚至违抗父命,也全然不听母亲的恳求和朋友们的劝阻。我的这种天性,似乎注定了我未来不幸的命运”——《鲁滨逊漂流记》——另一部我们耳熟能详的冒险传奇。 在“漂流”开始之前,两位主人公似乎有着相同的境遇:身处本国社会上层、与父亲有价值观冲突、与母亲相对亲近却得不到实质的精神支持、有朋友但不足以让自己坚定下来……
于是,“心理逃离”这个词跳跃出来,这个词也是解读《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疑问的第一把钥匙——为何狂风骤雨、惊涛骇浪之后,只有“派”一个人活了下来?(鲁滨逊也是如此)——当人无法在周遭的世界被认同,便会从人群中“心理逃离”出来,独享自己的精神世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就是给了“派”一次机会,让他得以尽情折腾。
既然是内心世界的畅游,对于这个终日奇思妙想的“派”,对于我们所能承受的抽象,我们可以大胆猜测,他的出发也许根本就没有他的父母、兄长这回事!——这根本就不重要。
相反,当“派”被大浪卷入水底看到货船下沉的那一刻,伴随着惊恐,他的内心却应当是一种获取自由、远离束缚的快感,那沉坠的货船如牢笼般把“现实的冲突和一切阻碍、否定”全部拽入海底。
当然,“派”在海洋上的哭泣,对父母和兄长的呐喊,也是对远离亲人——发自肺腑,真的思念。
就这样,《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开始了。
海洋之大,像人的内心世界没边没沿,一旦逃离束缚被释放出来,方觉慌了手脚,丢了航向。“派”就这样开始了浮萍般的随波逐流——无法预知终点,于是恐惧来了。
知惧的人,大多是内心细腻、情感丰富的人。“派”的“多元思维”,让他脑海中一切天马行空的构想和情绪得以在海洋中尽情上演:那种情绪如电掣雷鸣般的“挣扎”、如乘风破浪般的“反抗”、如止水似镜的“稍许安静”、如荧光世界的“诸多离奇”、如闲逛食人岛的“忘我的疯狂”……这“挣扎”、“反抗”、“稍许安静”、“诸多离奇”、“忘我的疯狂”全部来自于激情,这激情全部来自于青春,于是有了我们习以为常的那句话:“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漂流记”。所以,那些青春年少即能出发的人,“不幸”的背面又充满了世人的艳羡。
现实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每一次唯美画面的出现,在给我们带来视觉震撼的同时,都一次次加剧了“派”的恐惧。
你可曾想着他是在一个上不触天、下不接地的幽谧的海洋中。
越是恐惧越需要找个伙伴,于是斑马跳到船上摔断了腿、大猩猩坐着香蕉抑郁而来、鬣狗鬼使神差的躲在帐篷下、“派”在情愿与不情愿当中把老虎拉上了船……好吧,权且不想这些装在货船底层并且被笼子紧锁的动物为何会逃离出来,这只能佩服“派”的想象力了。
接下来,在这些“小伙伴”之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跟我们讲了血淋淋的“社会生存”法则:混乱的场面中,来自不同世界的伙伴,很难达成有效的共识,即便包括“派”在内的幸存者,本性和利益纷争让它们除了在心底残留一点同情之外,别无他法。于是,猎狗趁人之危主动攻击、各个击破,斑马心有不甘含恨而去,猩猩愤怒中透露出绝望。“派”则逃离现场,隔岸观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老虎最后的突袭,一招毙命的手法,让鬣狗猝不及防,很显然,这场战斗最终的胜利者是老虎。到此为止,船上只剩下了老虎和“派”。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亦真亦幻的讲述了两个故事版本,老虎也好,厨子也罢,真正的“强者”与暂时的“弱者”开始了对峙,境遇让他们容忍彼此的存在,渐渐发展为相互依存,更甚在老虎奄奄一息的时候,“派”和它相互依偎。若虎为人,心肠也该软了,若虎为虎,奄奄一息的它也当觉着点点温暖,一如它刚刚降临到世界上依偎着虎妈妈,那应当是一种熟悉的味道。
泊岸后,老虎驻足了一会,头也不回的钻入树林中。多少人颇有遗憾。可老虎为什么要回头呢?如果老虎抽象成一个“坏人的品质”,纵然他感受到人情的温暖,他也未必会放下凶残的本性,而对他而言,没有对派下手,已然是心灵感恩了;如果老虎抽象成“恐惧”,“派”已然在“漂流”中战胜恐惧,此时已经登岸,恐惧岂有再回头的道理。
有人说,是信仰救了“派”,我以为所谓信仰,从来都是由心而发的自救。这既能回答为什么有些人总说他感到神的存在,而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谁也求证不出真的事实。如果我们一定要说是信仰解救了一切,那么在哪里能找到信仰?只有危险的地方才能,只有孤独的时候才能,只有活下来的时候才能。当你无处躲藏的时候,“求生”会让你坚定“信仰”,每一次从濒死中逃离出来,都会让你更加相信上帝的存在。
人所习惯于将“不可置信的改变”归结成外力(信仰)助推的结果,那些不容易看得见的“量变到质量的过程”,人习惯于将他神话,甚至顶礼膜拜。其实,一切都是“自救”的结果。
所谓天意,只是概率性事件。
所谓信仰,其实是真的自救!
当海洋抽象成了一面镜子,心境变,海洋则变,你若深邃,海洋便幽深,你若恐惧,海洋便是惊涛骇浪,你若安生,海洋便是风平浪静。
所以,“自救”让“派”最终靠岸。而另外一个隐形的推力也断然不能忽视——那是将他拉回来的重要力量——“洋流”——这个一直存在于“派”的周边,却全然看不见的“社会暖流”。对于无数像“派”一样的少年,对于那些我们曾经都有过的叛逆、质疑,是“社会暖流”让我们一次次找回真实,回归正轨。这暖流,有可能是你的家人、朋友、甚至陌生人。
然后,我们会深刻的体会:“……我觉得,我们对于所需要得东西感到不满足,都是由于人们对于已经得到得东西缺乏感激之心。”——《鲁滨逊漂流记》。
这便是文明人的尴尬,唯“漂流”无以自救的“人生”。
可是,人,是不是应当去畅快一回?
少年派奇幻漂流影评 篇3
文/方聿南
《少年派》结尾抖开大包袱,四座皆惊(由此也看出原着小说人气还不够旺),这叙事技巧,让人想起《第六感》、《蔷花,红莲》等“所见未必所得”的悬疑片,但后两者是有一个确定真相,而《少年派》缺乏一个“官方”事实,因而更接近《全面回忆》《禁闭岛》以及《盗梦空间》的结尾部分玩的影像游戏,即一个故事的表象下,隐藏着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故事,再添上一抹开放式尾声,令整部影片衍生出两种势均力敌的可能,无论你采信哪种说法,总能找到大量细节佐证,足以叫观众陷入苦思,难得其解。
李安并不是第一次尝试这种“双故事片”,《卧虎藏龙》仗义行侠的叙事下,隐藏着寻欢不成的哀伤,《绿巨人》冲破枷锁的。战斗中,也暗含着蛇蝎女的隐喻,加上《少年派》,可以合称为李安的“双故事片三部曲”。巧的是,这恰是李安最注重视觉效果、最具商业卖相的三部作品,()分别充满了令人振奋的特效,《卧》是打破传统的飞檐走壁和武打,《绿》是高科技军事装备和怪兽搏斗,《派》则有海上灾难和奇异美景,还是3D呈现,无不洋溢着浓郁商业气息。也许是担心最拿手的人文表达被掩盖在极具冲击的动作特效中,李安才选择用双故事的手法处理这三部作品,这是他作为一个文人,自然而然的创作诉求。
比较起来,《卧》和《绿》更贴近《全面回忆》,即用一套影像系统讲述两个泾渭分明的故事,而《派》囿于原着,两个故事反差极大,无法照搬该模式,只能让其中一种诠释只存在观众想象空间。但影片仍做了不少努力,让观众在内心描摹那些未看见的场景时有据可依,两个故事的细节如齿轮般咬合,登船动物与幸存者的一一对应,动物不同寻常的举止,主角对猴子问“你儿子呢”,神秘岛的属性和形状对“人食人”的暗示,老虎显而易见象征了主角内心的恐惧。如果观众采信“现实版”故事,影片堪称完美的展示了人类思维强大的主观力量,可以将事实扭至如此偏离,仍能自圆其说。可想而知,那可怖的同类相残相食惨剧,何等触目惊心,一想起就令人浑身发抖,强烈反感下依靠潜意识的“美化”将其淡忘,是最自然的生理反应。
“双故事片”三部曲都由原着改编而来,有趣的是,《卧》小说并没有兜兜转转的暧昧叙事,也从没听漫画读者如电影般解读《绿巨人》,而《派》的原着小说虽也有两套事实阐述,但对第二种有更多细致入微的描写,读者在心理上更容易偏向现实版的残酷遭遇,那是作者的立场:信仰激发的正能量是对抗冰冷现实的有力武器,但毕竟不能取代现实,绝境逃生后,真相得到了还原。电影减少了第二个故事施加的心理砝码,这一方面是基于影片分级的需要,《派》虽然没有定位成阖家观赏,但暴力场面十分温和,兽类厮杀、人虎搏斗都用镜头语言点到为止,强酸池中群鱼葬身、树果中惊现人齿,非但没有一丝血腥,反而唯美如梦境。“奇幻版”尚且如此,“现实版”当然更是精炼越好,将之弱化的直接结果是,两个真相势均力敌,诞生一部工整典型的“双故事片”。当然,李安作品大都不是本人编剧,但我相信剧作的脉络走向,是他积极授意的结果。
奇幻故事大行其道,顺理成章的端出许多如诗如画的海洋仙境,有人对其总出现在波澜平静时表示不满,其实这是剧作需要,试想狂风暴雨时,主角忙着求生,与自然搏斗,哪还有精力编织白日梦呢?将闪电看做天启,已是最大发挥了。盛赞本片的卡梅隆一定是“现实版”的笃信者,有什么比天马行空的幻境更适合用3D来表现呢。我猜想老卡一定觉得,《阿凡达》再牛,描绘的仍是外星球上的“实景”,比起本片的以3D造梦,倒像是杀鸡用牛刀了。老卡大概也不是个“上帝的孩子”,否则他不会喊出那句着名的“我是世界之王”。
影片最后一个镜头,老虎跃入丛林隐没,画面故意停留了几秒,似乎预示着它将回头一望,但终究只是个玩笑。沐浴在家庭温情中的派已从恐惧中逃离,已完成了人生的考验和放下,细致讲起时也会动情落泪,但也有“发生就发生了,问那么多意义干嘛”的台词。然而作为观众却无法不进一步追问和思索。片中作家一角等同观众视角,经历了听故事全程。大部分时间他做的十分称职,这故事前戏较长,又由于埋藏许多线索、前后照应而不能舍去,他还在观众嫌闷时适时来句“你已经讲了名字的来源,登上了去加拿大的船”,替大家抱怨派不快点入正题。但故事讲完,他作为角色必须有所抉择,因而偏离了代表观众的职责。他选择相信第一个故事,但并非所有观众都有信仰,或有基于上帝的信仰,理解出现了分叉。
《全面回忆》等烧脑电影讲究逻辑推演,还原真相是理科生的俱乐部活动,而李安的双故事片看重感情依托,讨论起来,酷似文科生上研习班。《卧》的真相取决于观众对道家文化的诠释,《绿》的阴谋论来源于观众对两性关系的态度,《派》归结于信仰,都不是光靠事理逻辑就能说得通的,互持异见者也不大可能用辩论说服对方。说来说去,还是“信则有不信则无”,“心诚则灵”等老话的一次重新演绎。执着的扞卫自己认同的解释,固然是一种乐趣,但笔者看来,又何必非要有个结果,对世界的认知保留一份朦胧,也正是许多积极乐观者采取的人生态度,也许这是李安拍摄双故事片的初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