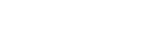《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生命韵律散文》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生命韵律散文
在南疆生活的两年多里,曾两次接触塔克拉玛干沙漠。
第一次是2007年8月初,到尉犁县罗布人村寨,那只是站在沙漠的一角,往沙漠里匆匆一瞥。当时的印象是,那里的沙丘和我小时候在家乡见到的沙崮堆相似,差别之在于,我家乡只有一座沙崮堆,而那里有许许多多的沙丘,连绵无穷。
第二次是2007年11月3日,顺着沙漠公路进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约三十公里左右的区域,在这里向四处观望,都是望不到头的沙漠,真正体验到了置身沙漠之中,如荡金色海洋的感觉。
站在沙漠中,四处遥望,瀚海无垠,起伏连绵,似乎是一首平仄跌宕、节奏舒缓、韵律绵邈的长诗。那隆起的许多沙丘,有月牙形,有金字塔形,有盆缶、盘碟、坟丘、堤坝等各种复杂形状,就像手写的音符,长短高低,卷曲弯拢,各不相同,排列在一起,就是一张奇异的乐谱。
脚下的金黄色的沙土地面,鱼鳞样的清晰纹络,一条条,起伏排列,脉络有致。那是造物主轻轻地喘息,在这金色瀚海激起的微澜。
在这金色的大漠背景里,时不时的还有一簇簇红柳,那深重的红,在金色大背景的衬托下,极具视觉冲击力,沙场红色战旗一般耀眼。更震人心魄的是那些枯死的红柳的主干或枝条,尽管身躯已残缺不全,甚至断裂劈叉,裸露着惨白的脊骨,但依然不减刚硬倔强的气魄,或昂扬伫立,或挣拽出扭曲倾仄,纠葛缠结的姿势。这种色彩和气魄,便令人想起了《命运交响曲》的嘭嘭作响,扣人心弦的主旋律。
我们去沙漠的两次,都是微风天气。在微风的时候,表面看,沙漠是沉静死寂的。我坐在松软的沙丘上,静下心来,静静地注视沙丘的脊梁,发现那起伏弯曲的沙梁,在不断地扭曲变形,那是因为一些细沙在悄悄地涌动。我禁不住趴在沙丘上,静心屏气,仔细观察。只见微风轻拂下,细沙如水一样脉脉漂移。因为头部离沙壤太近的缘故,细沙竟然吹拂到我的脸上。侧耳细听,于寂静无声处似乎谛听到地底蛩音——那不是蟋蟀的浅唱,那是微风吹拂细沙的低吟!我没有用录像拍出动态流动的过程,而是用相机逆光拍下了微风轻拂,细沙漂移的一张张静止画面,倘若前后相续,仔细观察,我相信,任何一个读者都会发现那极细微的动态差别。
我终于明白,沙漠原来也有它自己的生命之歌,有它自己的生命韵律。
当然,在这里,还可见到沙漠公路两旁的绿色植物带,见到苍劲的胡杨,见到红柳坟和芦苇丛,见到植物生命的印记。据说,越过几十公里的沙漠公路绿色植物带,越往沙漠腹地走,大漠就越显得冷酷无情,越被刻骨铭心的死寂所笼罩,绿色生命的印迹越来越少,最终几近于无。除了沙丘还是沙丘,除了沙漠还是沙漠,最终露出“死亡之海”的本色。当然,也是金色瀚海的本来面目。但,我相信那里,即使无风或微风的时候,也一定有一双无形的手,拨动着自然变化的琴弦,弹奏着生命呼吸的旋律。
其实,沙漠本就是流动的'海。狂风大作的时候,细沙随风,卷裹呼啸,飘摇而起,转眼之间,丘陵可以削减成洼地,洼地可以隆起变丘陵。庄子曰:“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庄子以“息”写风,极富表现力,这里的“息”就可以理解成造物主的气息,自然界是靠风来呼吸的,这一呼一吸之间,便有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这一呼一吸之间,便有沙漠的流转变动;这一呼一吸,就有了沙漠的动态韵律。当年彭加木失踪之后,我们国家派了许多人,许多架飞机,都杳无踪迹,不正是因为这种沧桑巨变,无情掩埋了一个伟大而又渺小的生命吗?
所以,不管沙漠的动态韵律,能给风流骚客带来审美欣赏也罢,能给探险家带来悲剧命运也罢,它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流动取向,它的主宰是造物主,是自然界,自然界的一呼一吸决定着它的生命韵律。造物主情绪激烈时,它便猛呼狂哮,摧枯拉朽。尘沙身不由己,随之漫天飞扬,如野马奔腾,如群虎下山,飞卷削刮,腾转闪挪,丘陵与洼地,只在转眼之间,即可变异易位。此时,它所弹奏出的是音调震耳,节奏迅猛的狂飙进行曲。造物主心绪安静,它便喘息轻缓。尘沙只是暗流涌动,悄然挪移,弹奏出“蒙着轻纱的梦”一样的舒缓小夜曲。无论如何,它决不会绝对静止不变,运动是它的主旋律。
由它想开去,是否可以推论,世间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生命流动的韵律?